刚下过一场雪,凌晨三点多,罗正宇打开房门,走上楼梯,在旅店的楼顶徘徊。
4点23分,他返回房间,在手机便签上写下遗言:我去死了。自杀的。在武汉玩了一年。什么事没做。没什么遗产留下。借了一屁股债,不会还了。我太幼稚了,大人和我说的都是对的。可惜我明白太晚。都是我自己的错。对不起……
第二次,他又爬上楼顶,5点00分,再次返回房间,在便签上写道:老板,你立即报警吧,我在顶楼上吊自杀了,对不起……之后,罗正宇第三次爬上楼顶,没有再走下来。
2018年1月29日,早上七点左右,旅店工作人员到阁楼收被单,看见罗正宇悬挂在阁楼外的房梁上,脖子上套着一根白色的登山绳子,已经没了呼吸。

悬挂的登山绳子和房梁。
最后的日子

上海路的两边,大多是一些老房子。武汉江岸区上海路,夹在江汉路步行街和汉口沿江大道(长江外滩)之间,是闹市里的僻静处。
三层楼的惠风旅馆(化名)邻近一家天主教堂,看起来有些老旧。老板黄生铭说,旅馆开了十几年。
1月23日,罗正宇拖着一个深蓝色的箱子走进来,问黄生铭住一个晚上要多少钱。黄看了他几眼, “很平常的一个小伙子”,大概一米七,和他差不多,神情举止也没什么异常。
黄生铭对罗正宇说,58块钱一个晚上,最终又便宜了3块钱,给他算55块钱住下了。旅店对面的一家酒店,最低消费为118元一晚。
第二天早上,黄生铭问罗正宇是否要续住,罗说他还要住几个晚上,房费再便宜点。黄生铭又给他少算了五块钱,罗正宇付了200块钱,一共四晚的房费。
房间在一楼,不到五平方米,里面有一张床,一张桌子,桌上是一台老式电视,电视后面隔出了一个洗手间。
开始的两天,罗正宇每天早上出去,到后面两天,他几乎不出门了。每天下午两点,黄生铭会敲所有房客的门,检查一下。他看到,罗正宇的房间开着灯,他边上放了一小袋零食,旁边还有一瓶矿泉水。
旅馆对面,有一家炸酱面馆、一家便利店和超市,还有一个生鲜综合市场。罗正宇经常逛这些地方,他有时消费几块、几十块,有时消费一百多,都是电子支付。

罗正宇经常去的炸酱面馆,中午和晚上有盒饭吃。1月28日早上六点,罗正宇在旅店对面的炸酱面馆吃了一份早餐,一共消费了6块钱。杂酱面馆的李老板说,每天来吃的人很多,但他肯定罗正宇来过,“如果人在这里,我说不定就能认出他来”。
那天他回到旅店时,大约早上七点,黄生铭对他说,“你不要住了,你又不(出)去做事,早点回家算了”。罗正宇回说,他还要再住一个晚上,要换一个房间,住的一楼晚上有老鼠,之后他又用支付宝付了50块钱房费。
罗正宇曾在1月19日给父亲罗立军打电话,发现他手机欠费,帮父亲充了100元话费后,两人在电话里约好:罗立军1月30日晚上10时到武汉,罗正宇到时去火车站接他,在武汉游玩几天。
罗正宇还在1月27日给爷爷打过电话,说自己2月8日回老家天门市小板镇。这通电话只打了几分钟,听上去很寻常。
两天后的1月29日,上午9点多,在浙江绍兴打工的罗立军接到武汉上海街派出所的电话,说他的儿子罗正宇自杀了。这是两人约定见面的前一天。
罗立军不相信,以为是诈骗电话,但他担心儿子真出事,想起住上海路附近的儿子高中同学刘文峰,罗立军立即给他打了电话,拜托他去上海街派出所看看。
那天是周一,地上很多积雪。刘文峰走了十几分钟,到了辖区派出所,一位民警叫他上二楼刑侦科,刘文峰当时想:难道罗正宇一年不见,去搞传销被抓了?
两人上一次见面还是一年前,2017年2月的一天,罗正宇从浙江杭州回到武汉,把他带回来的行李放在刘租住的房子里。此时,罗正宇已从杭州的原单位辞职,打算在武汉转行学计算机软件开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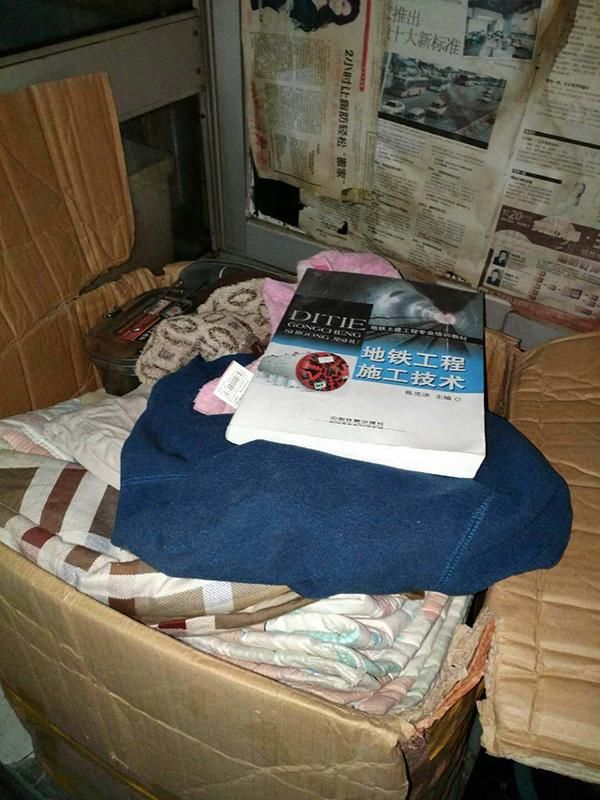
罗正宇回武汉时,放了袋东西到同学刘文峰租住的地方,至今都没有取回。里面有被子、衣服,和一本《地铁工程施工技术》的书。派出所民警翻出几张照片,照片里的罗正宇悬挂在房梁上,刘文峰瞬间趴倒在地上。
黄生铭检查罗正宇手机时发现,他的支付宝余额只剩下七毛一分钱。罗正宇自杀时穿一件酱色棉袄,“破破烂烂的”,当天上午九点,派出所民警和法医赶来做完尸检,才把他的遗体放了下来。
两天后,武汉江岸区警方通过当地媒体发布消息,罗正宇系自杀身亡。

罗正宇的蓝色背包,只剩下一块钱和一颗大白兔奶糖。
从杭州到武汉
2016年夏天,23岁的罗正宇从武汉理工大学交通运输工程专业硕士毕业。
他们专业就业前景不错,罗正宇是本硕连读,毕业后进了一家大型国企,总部在武汉。他以技术员的身份进到下属的城市轨道工程有限公司,之后被分到杭州项目部,离他父亲打工所在的绍兴不远。
入职两月后,罗立军去杭州看儿子,感觉罗正宇状态“很不错”,就是脸上晒黑了一些。“手机里还记录走了多少步,他说今天走了一万步。”那天他去了罗正宇宿舍,宿舍里有四张床,有空调、洗衣机,感觉和大学宿舍差不多。
也许罗正宇没有流露他的烦恼。一个月后,前同事陈晓勇在项目部见到罗正宇,罗说起自己经常加班,晚上整理资料到很晚,白天又要到工地上做测量,工作和他所学专业关系也不大。
2016年11月,罗正宇突然跟父亲说,他想辞职不干了,父子在电话里说了四十多分钟,罗立军不停地劝儿子。几天过后,他和弟弟专门请假到杭州劝,还是没有用,罗正宇坚持要辞职,“他说,就像没上过这六年大学,到武汉学(计算机)编程,重新学一门手艺”。
2016年12月,罗正宇在大学好友群里抱怨:工地工作环境差,一个月工资才五千多块钱,比他一个部门的本科生高17块钱。他打算年后辞职,回武汉报计算机编程培训班,转行计算机软件开发,或搞智能交通,还称自己在看计算机二级等级考试教程。
当时群里有一个同学回应:自学的,又没有具有说服力的(计算机)软件使用经验,恐怕不怎么好找工作。

2016年12月,罗正宇在大学QQ群里的聊天记录。2017年2月,罗正宇又在QQ上问同学蒋辉:现在报java培训班转行,你觉得靠谱吗?蒋辉回复他说:不靠谱……学java再失败咋办。罗正宇说:他不知道,现在也比较纠结。
一个月后,罗在群里告诉同学,他又回了杭州的原单位,每天忙得要死。群里有人@他,问他想不想跳槽做交通规划,罗正宇没有回复。
2017年8月,群里人再次@罗正宇,问他在哪里,他说还在杭州的原单位。

2017年8月,罗正宇在大学QQ群里称,自己依旧还在杭州上班。事实上,罗正宇在2月就离职了。罗正宇原单位总部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澎湃新闻,此前他主要负责现场技术管理,技术交底,施工生产的监督等,平均每个月工资税后5400元左右。单位包食宿,有自己的食堂、健身房、图书阅览室等,不过建筑行业工作比较辛苦,而且工地打交道的群体复杂,流动性大,很多刚毕业的人来了后,因为希望有一个安定的工作环境,离职的也比较多。
离职之后,罗正宇去了哪里?谁也说不清。
2017年的大年三十(1月27日),罗家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,罗正宇第一次主动向家里各位长辈敬酒。正月十九,他背着背包离开了家,临走前告诉家里人,他已联系好了武汉达内培训机构,准备去学三个月的计算机编程再在武汉找工作。
但3月5日,澎湃新闻记者联系到武汉达内培训机构工作人员,对方回复称罗正宇没有在他们机构培训过。
爷爷罗成民每月都会跟罗正宇通电话。2017年夏天,罗正宇在电话里告诉爷爷,他去面试了两家公司,被其中一家公司拒绝了,进了另外一家公司,试用期每个月一千五百元。
2017年8月24日,罗立军问儿子在哪儿工作,罗正宇告诉父亲,他在武汉亿网计算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班。
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,前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:计算机软件开发;计算机安装、调试;计算机及相关服务。3月5日,该公司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记者,他们从未聘用过罗正宇,但不记得罗是否去他们公司面试过。
谜团与印记
罗正宇的离去成了谜团,只给家人、朋友和同学留下深深浅浅的记忆片段。
罗正宇3岁时,父母离异,此后极少见到母亲,父亲陪伴他的时间也很少。父亲再婚后,他跟继母关系不是很好,“很少叫她”。
罗立军去浙江绍兴打工的十几年,罗正宇一直由爷爷奶奶带大。爷爷罗成民起初在村里教书,罗正宇上小学时,他调入镇中心小学,罗正宇也跟着爷爷奶奶住到了学校。在爷爷印象里,罗正宇“老实听话,从来不说假话”。
家里的同辈中,罗正宇和堂弟罗春宇关系最好,两人经常一起聊学习、游戏、电影,好到“同睡一张床,同穿一条裤”。但罗春宇觉得,哥哥把很多事情和想法憋在心里,“没有一个人真正走进过他的内心”。
罗正宇成绩很好,高中同学刘文峰记得,那时大家都青春年少,唯一的任务就是学习,罗正宇偶尔去网吧玩游戏,仍能考班级一二名。
2010年6月,罗正宇以将近600分的成绩考入武汉理工大学,母亲刘芬芬知道后,托人送来了四千块钱。刘芬芬说,罗正宇读小学的时候,她曾到家里来,提出想见儿子,被罗正宇的奶奶拒绝,说不应该让罗正宇分心。此后她又来了一次,没有见到儿子,之后她便不怎么来了,只让人不时的打听他的境况,还托人给罗正宇送过绣着“正宇”名字的衣服。
本硕连读的六年,罗正宇没有谈过女朋友,同学介绍女孩跟他认识,他几乎都不跟对方搭讪。罗春宇记得,有一次,他去学校看哥哥,室友告诉他,你哥找了好几个女朋友,“我说不信,他就一脸尴尬地笑着说,‘他不会信的’。”
在大学同学唐力印象里,罗正宇有些内向,跟人说话有时会害羞。不过刘文峰说,罗正宇跟不熟悉的人不爱说话,但跟熟悉的人一起话很多,而且很“逗比”。他至今记得,有一次,罗正宇和室友打赌,说自己可以从寝室穿门而过,“结果他从门上面的窗户爬到外面的阳台”。
读研时,罗正宇拿过学校奖学金。2015年3月,他被评为武汉理工大学“研究生元旦晚会优秀工作者”,当年11月,又被评为“武汉理工大学校三好研究生”。研究生导师杜志刚眼中的罗正宇,是一位优秀的学生。

罗正宇读研究生时获得的荣誉证书。毕业后,罗正宇没再单独联系过导师,只偶尔在群里说上几句。到了2017年,他几乎不在群里“冒泡”了,像突然消失了一样。
2017年3月,罗正宇的高中、大学同学肖勇打电话给罗正宇,问他在哪儿?罗正宇说,他已回杭州原单位。此后的几个月,他们不时在QQ上聊,还一起玩游戏。罗正宇会玩的游戏很多,他和肖勇一起玩“dota”--一种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。
事发前十天,1月19日,肖勇在QQ上和罗正宇聊游戏,肖勇催罗正宇快点,罗正宇回复说:哥死了……肖勇回了一个表情,罗正宇接着发了一条:哥现在(对)什么都没兴趣了啊。
当时,肖勇没有回复--他们之间偶尔会跟对方抱怨人生,这次他也没有在意。在肖勇印象里,罗正宇乐观,凡事看得开。
1月21日,罗正宇给肖勇发出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条QQ信息:唉,悲哀……
借贷与催债
罗立军有三兄弟,两个弟弟每人一个孩子,只有他有两个孩子--再婚后,他又生了一个女儿。
父母为了照顾罗立军,把罗正宇当亲生儿子一样带,“爷爷每个月有退休工资,还出去赚钱,就想以后为他结婚买房。”罗立军说,他们没跟罗正宇说过,但家里人都心知肚明。
“他有什么想不通的,为什么要走这条路……”奶奶哽咽道。
2017年正月19日,罗春宇和哥哥罗正宇一起离家搭车去武汉,罗春宇此时在武汉读大学,罗正宇说联系好了计算机培训学校,此后两人没有再见过一面。“我一直以为他工作很忙。”罗春宇痛惜地说,他不知道哥哥一整年靠借贷过日子。
支付宝的消费记录显示,2017年一整年,罗正宇主要在江汉路、胜利街、上海路等一带辗转,常去附近的网咖、便利店、炸酱面馆、水果店等消费。其中一家距离旅馆不到100米的网咖,罗正宇从2017年2月,一直到他走前最后一个月,支付宝都有消费记录。
这家网咖不大,里面有不超过五十台电脑,弧形的超大屏幕,下载有各种游戏。上网分三个档次,五块钱、六块钱和八块钱一个小时;五元区包夜14元,六元区包夜18元,八元区包夜20元。罗正宇或许无数次在这里度过了他的漫漫长夜。
3月2日,该网咖网管对澎湃新闻记者说,他们每天进进出出一百多人,不记得有一个叫罗正宇的人来过。
支付宝收支记录显示,2017年3、4、5月份,罗正宇的收入几乎为零,每个月支出两三千块钱;从6月份开始,每个月收入有一两千块钱,支出上涨到四千多到六千多元不等,且每个月都在还蚂蚁借呗和花呗;变化从2017年12月开始,支付宝里收入依旧是两千多元,但支出达一万二千多元,2018年1月,收入上升为六千多元,支出同样也是一万两千多元。从支付宝消费可以看出,消费增多主要是各种还贷,以及生活开支。

罗正宇2018年1月的支付宝账单。罗正宇手机里,金融理财栏里有13个网贷APP。
据此前媒体报道,13个网贷APP里有五万多元的分期欠款,大多是2017年12月和2018年1月所欠的。截至2月28日,罗正宇欠下的将近四万元的分期欠款,依旧每天在短信提示还款。
除此之外,罗正宇还通过微信和QQ借款,一个叫“天誉金融”的QQ账号曾跟罗正宇聊天称,5000元起步,7000元到手5000元,七天还7000元,日利率达285%。另一个叫“盛世钱庄”的账号称,3000元到手2100元,七天期限,押金1000元。
2017年12月16日,罗正宇在微信上跟一匿名用户聊天,对方建议他办信用卡,罗正宇回复:我还是不办信用卡吧,不想给朋友知道我借钱了……
12月21日,罗正宇在微信跟前同事黄小兵聊天,对方问他在做什么工作,他说在武汉搞计算机,“还不如在工地,经常加班,看电脑一看一整天,工资也低……”
大家事后回想,或许他一直在武汉流浪,根本就没有上过班。没有人知道,他是如何度过这孤寂又绝望的一年。
“天誉金融”曾在QQ上联系罗正宇,没有得到回复,之后连续发送了多条信息:小伙子可以的。硕士?就这样?读书读成这样?你等着上门吧。
1月31日,一个名为“A清收客服-安主管”的微信账号向他接连发出问号,之后不断发送信息:“等着,大年三十,群发你!!”2月2日,该账号接着发信息:我就是对你太好了,年前没有给我清帐的,我能让你过个好年,我跟你姓!!

2月1日,催债者通过微信发来的信息。此时,罗正宇已经过世了四天。
3月7日,澎湃新闻记者联系到该收客服主管,对方拒绝回答问题。
罗立军说,罗正宇走后的第二天,他在儿子的朋友圈里发了一张“遗体接运冷藏协议书”的照片,之后依旧不时接到催帐电话。
尾声
罗正宇的家是天门市小板镇金科村一栋两层的白色楼房,前面有三颗梧桐树。从天门市到这里不到十公里路,四五年前,村里建了一座汽车城,从去年10月开始,罗成民每晚都到汽车城上班,他帮汽车修理厂看门,每个月工资一千多块钱。
家里很简陋,堂屋有一张黑色桌子和八张凳子,那还是十几年前,罗成民自己打造的,墙壁上挂了一副硕大的十字绣,上面绣着“旭日东升”几个字,也是罗成民自己绣的。
从楼梯上二楼,是罗正宇和堂弟睡觉的房间,里面摆设很少,罗立军指着一张桌子说,兄弟俩平时在这里看电脑,更多的时候,他们跑去网吧玩游戏。
罗立军说,他很早以前就意识到,儿子交织在亲人的关心和恩怨中,家庭对他的影响很大。为此,他从前经常给罗正宇买书,后来又经常给他写信,但父子之间总是很少谈心。
罗正宇从杭州辞职后,罗立军为不给儿子压力,很少过问他工作上的事,一般都是节假日发个信息,问他怎么过,平时冷了,提醒他加衣服,并告诉他,要跟同事搞好关系……
在罗正宇的房间,找到了一个他之前的笔记本,罗正宇在上面写道:你是一粒平凡的种子,和同伴一样萌芽于田间,春风吹来,遍地绿。你本来可以做一颗普通的小草,但是你不甘于平庸的依附于大地,你爱上了头顶那片深邃的蓝天,于是你努力地把根扎深,把枝叶向蓝天伸展……
但来不及把枝叶向蓝天伸展,罗正宇的人生戛然而止,最终停留在他24岁的记忆里。
1月22日,罗正宇通过QQ账号加了一个山东人,他跟对方说:你山东的啊,我武汉的,我还想找你一起,我一个人准备自缢,听说悬空瞬间就没感觉了。罗正宇手机文档里面,有一篇《完全自杀手册》,手册里介绍上吊自杀的准备、经过、感受、尸体状态等。
罗立军说,他对儿子自杀没有疑问,但怀疑他生前受到胁迫,他向警方申请调查相关情况,目前暂未有进一步信息。罗正宇自杀前几天,接到过多个外地陌生电话。澎湃新闻联系这些号码,均无法打通,或者无人接听。
罗正宇的母亲刘芬芬曾在2017年夏天的一个早上接到一个武汉打来电话。刘芬芬在睡梦中迷迷糊糊接通电话,对方那头没有说话,很快就挂断了,她紧接着回了过去,对方依旧不说话,之后又一次被挂掉了。
一直到罗正宇走后,二十多年未见面的前夫告诉刘芬芬,去年夏天那个电话是儿子罗正宇打来的。
2018年3月5日,罗立军再次来到上海路,在儿子曾经待过的地方来回走了三四遍,甚至还去了他理过发的地方,他花同样的价钱--35块钱,给自己也理了一个发。

罗正宇研究生毕业的班级合影。(除罗正宇、罗立军外,其余均为化名。)